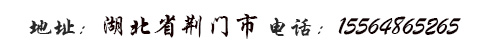陈浩草本人物
|
千羡万羡西江水,曾向景陵城下来。 陈浩,天门市干驿镇月池村五组人。 草本人物 村庄坐北朝南,北临牛蹄支河,往南依次是新沟、大滩、沉湖。先民择水而居,靠水吃水,与水生死相依。在这片不足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过生离与死别、谐谑与莽荡。 我出生晚,不曾目睹,道听途说,追录旧闻,以资备忘。 民国31年正月初三,焕庭爹陪新婚妻子回门,新郎长袍、马褂、礼帽、皮鞋,隆重其事,新娘大红袄裙、绣花鞋,夫在前,妻在后,需过桥到牛蹄河对面的村庄。夫走到桥上回身望妻,发现她一手提鞋,一手挈裙,从冬季枯水期的河滩淤泥中涉水而过。焕庭爹看着水中跋涉的野蛮新娘,扭头折返,初四就出门经商了。从此,萍飘蓬转,不通音问。传闻,被同行的结拜弟兄谋财害命,尸体扔入了长江。新娘子,就是后来的黄家婆,寡居终身。晨昏几番交替,沉沉风雨夜如年。此后,无数个耿耿星河欲曙天,她是否会无数次地踏入那个雾气沉沉之下的早春的河流,想起桥上的那个男人对自己最后的一瞥。 三个待字闺中的女子,因命运相同,父母重男轻女,家务事多,农活太重,有轻生念头了,相约赴水而死。在生死的交限,担心有人不坚决,中途反悔,三人用一根长绳牢牢捆绑在一起,身沉牛蹄河。她们不知道,生活就是这样,一帆风顺的人生又会有多少?生命是一张单程车票,一往无前,也一去不返。如此这般,是一念之差吗?求生者如求官,惟人所命;求死者如逃名,惟己所为。世间之事就是如此,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进入舞台、电视、报纸、网络,另外一些人,他们的目标却是离开。 大爹,祖父的长兄,以捕鱼为生,一日,与大婆拌嘴。“人家某某下一次湖南就赚好多钱。”“你姆妈,各有各的本事。”“你这砍脑壳的有什么本事呀!”“老子抠鳝鱼,全湾第一。”那种语气,好似他赴了琼林宴,打马御街,点了翰林,剑履上殿。老婆子若不苦守寒窑,一字并肩王就要马前泼水。寻常柴米夫妻,哪有什么深仇大恨。磕磕绊绊,生活如水,淙淙流过。拉扯大一帮子女,也就相看两不厌了。可怕的是,基因是有记忆的。他的儿子也是咬金不咬铁,与老婆斗争不输乃父。“你把这烟不喝不行吧?”“你把这气不透不行吧?”一个针尖,一个麦芒,大抵如此。 有一男青年,亲事不如意。五月的一个中午,在新沟踏水车。其母送午饭来,发觉他有些异样。于是,每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站在水车上的儿子,发现儿子也一直目送着自己。母与子,你走你的阳关道,我过我的独木桥。当晚,“悄立市桥人不识,一星如月看多时”。他吊死在了水车旁的草棚里,枕头下有绣花鞋垫两双,那里面一定有不为人知的令人落泪的温柔。马嵬坡下有冤魂,长生殿里痴情多。如果她知道那一天是儿子的末日,她一定会留下来。儿子打起了退堂鼓,她得敲响惊堂木。给他一个拥抱,看着他把一碗饭吃干净,还要陪他踏半个时辰的水车,踏平过不去的坎,磨磨叽叽,磨磨叽叽,拖散牛头马面的耐心。 陈家婆刚嫁过来时,也在大滩参加薅草,身材高大,鲜嫩茂盛,水分充足,与那广袤的齐膝的棉株相映成趣。着大红连衣裙,远远看去像一乘红漆陪嫁衣橱。隔一条河,在另一畦田里劳作的人们问其公爹:“这个新姑娘咋样?”公爹老眼昏花,答一句“可得哈”。此三字便成了新媳妇的绰号,伴其一生。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万众所瞩目的瞬间,也会有被坑被戏弄的时刻,迎着它走过去就是了,一样可以看到一树一树的花开。 祖父被抓壮丁,送到沔阳。某晚,与人合谋逃走。怕长官组织追捕,闯进连长卧室,枪杀连长。连长是河南人,祖父与他素味平生,只是在干驿皇殿军训时吃过连长的窝心拳。在襄河边,草草埋葬连长,选一匹好马,让连长老婆骑着回家。遣散全连所有丁夫,各归各家。未亡人的呜咽和身后江水的汩汩伴奏,使这群乌合之众心中萍翻桨乱,雨打魂幡。与同村某某互换肩膀,昼伏夜行,挑一担两只箩筐,跨越沉湖湿地回到家。村里谣言是一担银元。可信度不高。我家遭遇多次一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刻,有此一笔洋财,何必挂着干鱼吃白饭。祖父一生只杀过一个人,三十出头就病逝了。祖父去世六十多年了,没人记得他的血腥段子了。这些抢救性的记忆不会存留很久,一切向前看,谁会管一个人的前世今生。 农业合作社时期,向湖水要粮,沉湖被围垦。生产队组织到湖田插早秧,某人乘机拍了一下旁边妇女的臀部。该妇女一声呼唤,另外两名好姐妹加入,撵着男子围捕。其他人停下手中的活计,呐喊起哄。终于把他按在了一条涧沟里,解下他的裤带,缚住他的手脚,剐成赤膊精光,再往裆部抹一坨稀泥巴。原始的野性酣畅淋漓地迸发,角逐者和观众都感受到狂欢的魔性。天地自然山川草木之下,元气浩荡,返璞归真,如此真实,又如此匪夷所思。那样的年月,双抢、秋收、水利建设,战天斗地,却食不果腹,苦中作乐也是为了把生活这杯苦酒顺畅饮下。没人会想到伤风败俗、男盗女娼。偶尔疯魔,也没有人会上纲上线,也并没有导致礼崩乐坏。 刻印在石碑的名字也会腐朽,即便是文字,在图形摹声方面也有先天性的缺陷。一个人被记住很多年,也许就是因为人人心中有、人人嘴里无的一句话,也许就是因为嘶声裂肺也唤不回的离别,也许就是率性而为的偶尔癫狂。 今天,我们轻易抛弃掉不好的记忆,仍然不能更多的感受到生命的喜悦。好在,记忆是有根的,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就会牵藤爬蔓,开花结果。 唯有时间是真正的胜利者。无数个寂寂无名之人,在世间走一遭,如当年生当年死的草本植物,湮没于荒烟蔓草间。不管他们现在身处九霄云外,还是阴曹地府,当年露过的一鳞半爪,也曾经照亮过彼时彼地的一方天空。 天门文艺投稿邮箱: QQ.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lianqiancaoa.com/lqcyx/2889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九里香的主要虫害及防治
- 下一篇文章: 九里香盆景制作养护经验点滴